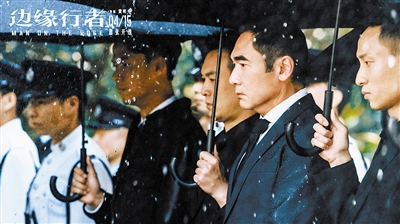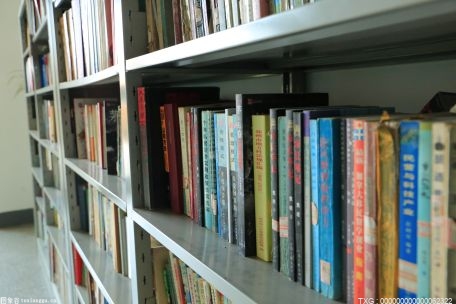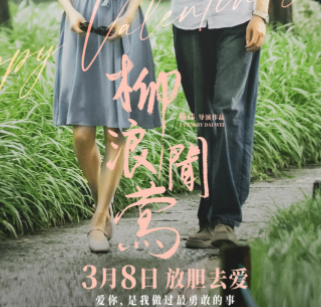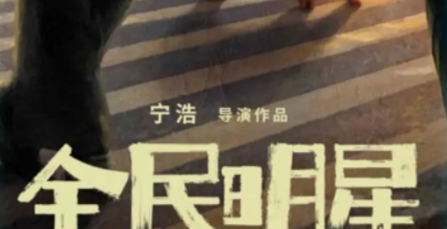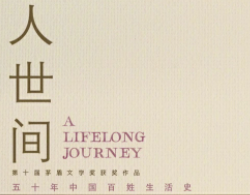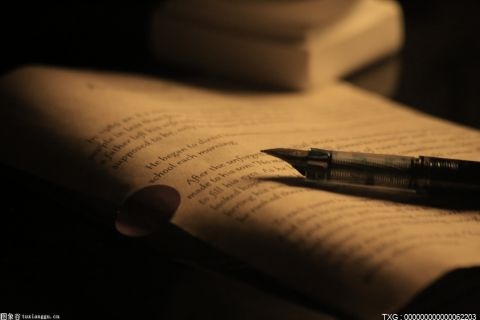《瀑布》和《美国女孩》在金马奖上杀得难解难分,最终前者大获全胜。同样是母女题材,背景同为疫情下的家庭困境,钟孟宏导演的《瀑布》对准当下的新冠,阮凤仪的《美国女孩》则回溯近20年前的非典。
当下华语电影中作者电影的代表人物钟孟宏,较之后辈阮凤仪,从剧本创作的丰满张力到演员的调度和激发,的确全面高出一筹,《瀑布》赢得最佳影片、最佳剧本和最佳女主角奖顺理成章。

《瀑布》像精心加工的食品,而《美国女孩》则像是田间地头端来的新鲜食物。《瀑布》中贾静雯、王净“母女”演技无疑更为精湛,但所说所做,还是带着导演刻意安排的加工痕迹,《美国女孩》中的母女三人更接近现实中女人和女孩子的言行。《美国女孩》正是编剧、导演阮凤仪根据个人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电影。
杨德昌、侯孝贤、李安、戈达尔、是枝裕和、达内兄弟……谈及其学养来源时,阮凤仪很是尊贤地举出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。《美国女孩》海报上姐姐伏在母亲膝头掏耳朵的形象,很难不让人想到杨德昌的《一一》,那里姐姐投入的膝头是婆婆的。
《一一》探讨了传统中国家庭面临现代化冲击时人与人之间关系何去何从,《美国女孩》对准的也是家庭成员,时间点直接放到冲击发生之后。旧日华语家庭片中常备的祖辈不见了,孩子们的姑妈、也就是女主人口中的大姐,虽然是这个家庭危难时的救火队员,却也只是被提及,并未有一秒钟出场。这也体现了新型家庭的伦理:手足之情是上一代家庭的产物,现在“家庭成员”的概念仅限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组合。
时代和社会是大背景,人物就是其中的图形。很多时候,有些图形合理地隐去,远胜把背景强行填满。和精简家庭同理,导演安排好心的邻居把小女儿送回家,女主人却是防备远大于感激,三言两语打发了,也断绝了日后走动的可能。从“健康写实主义”到台湾新浪潮,我们习惯的台湾电影中邻里之间其乐融融、守望相助的热络之姿,《美国女孩》中看不到了,因为现实中那个时代已经远去。
《美国女孩》从“梁芳仪”的视角展开,和侯孝贤借“何孝炎”讲述的半自传体电影《童年往事》如出一辙。至于侯孝贤对阮凤仪的潜移默化,恐怕更多是在镜头美学上:除了那个魔幻现实主义的高潮部分,是用一连串很王家卫的短打蒙太奇构建,贯穿《美国女孩》全片的长镜头、景深镜头和凝重的色调造成的迟滞感,都颇具传统中国审美——有意思的是,藉此赢得金马最佳摄影的,却是位希腊裔摄影师。
贯穿全片的女性视角,准确说是女孩视角,很大程度是通过运镜来实现的。多用平视高度、侧角度镜头,既是这个回流移民家庭的“美国女孩”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外化,也符合华人女性心理共性——无论年纪,无论身心,她们都更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够美的一面,而不是不够美的另一面,林嘉欣扮演的母亲患有绝症,有时要靠背影来表现身体衰弱。但需要表达时,她们绝不会像传统的男性尤其父亲那样,碍于面子和权威而吝于表达,这和李安拍郎雄时总是正面对准那张不苟言笑的老脸,还总让老爷子半眯着眼睛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当然,这里也有例外,比如展现梁芳仪因考试不及格接受体罚时,正面略俯角镜头直怼的简单粗暴程度和施暴者有一拼,展现从美国全A的资优生到吊车尾的落差和不被尊重理解的无助。值得一提的是,阮凤仪截取的不只是自己的成长一页,也是台湾历史社会的重要进程——就在此片反映的年代之后,岛内便爆发了针对教育界和军界在内的“反对体罚”运动。
值得称道的还有阮凤仪的国际视野。同样是处女长片,又都是移民家庭题材,她和《美国女孩》也自然地被拿来对标李安和《推手》。两部影片,两个同样寡言少语的开头交代了人物关系,展现背景差异造成的隔膜,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《推手》里直到语言不通的老公公误拿锡纸热饭、差点引发微波炉爆炸,才让洋媳妇说出第一句对话,家庭成员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相邻房间各行其是。阮凤仪虽然安排了纵向单线叙事,也同样构造了并行空间:台北机场行李转盘前,母亲一再嘱咐自小长在美国的姐妹俩:“当着爸爸,要讲中文”;而接母女三人的爸爸,车里习惯的“本地新闻”则来自他常年打拼的深圳。对未来生活不适的不只是两个年幼的“美国女孩”,躺在一张床上的夫妻二人不见惯常的小别胜新婚,草草交流几句琐事便各自睡去,这也为之后更加黯淡的剧情进程埋下了伏笔。
阮凤仪毕业于台大中文系,也曾就读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,正是那个期间走进法语电影的广阔天地。几年后,她在《美国女孩》中安排自己的化身来了一次前往梦中彼岸的叛逆之旅。
让俗务所累的小人物在荣誉遭受危险的时候,却能如哈姆雷特一般迸发出黯淡的光芒、卑微的伟大,这一点颇具达内兄弟之风范。剧中林嘉欣像我们熟悉的其他“失败母亲”一样,崩溃时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“还不是为了你们”,但在出席家长会时,听到“不打不成器,老师你就给我打”的民意,还被“好学生”家长请托不要让你家孩子耽误我家孩子时,终于奋起反击,既是保护家庭成员的应有之义,也一展自己初代“美国女孩”本色。
姐妹俩成长时一直缺位、在母女矛盾中也基本和稀泥的父亲,在病妻等待手术时本能地推开她冰冷无助的手,让观众都不能忍;也在母女矛盾爆发时,第一次从画面的边缘走到C位,动手惩罚了女儿的莽撞失言。他站出来的理由并不是传统华人家庭讲究的“我是一家之主”,而是“我是我妻子的丈夫”,也展现了“夫妻高于亲子”的新型家庭伦理。
能成为年代佳作甚至时代佳作的电影,都能在艺术表现的精微之处见时代大势、大义。除了家庭形态和伦理变迁,台湾电影中曾经反复咀嚼、如今却大大弱化的认同感这一母题,被阮凤仪和《美国女孩》再度拾起。比起《童年往事》中从纠结于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、“只把杭州作汴州”的何家祖孙三代,《美国女孩》梁家四人幸运在,虽然同样面临适应、挑战甚至落差,起码还可以选择。
对每一位新导演而言,一个惊艳的开始之后,“二年级”才是真正的考验。阮凤仪的电影里,有着从“四小龙”时代的“来来来,来台大;去去去,去美国”,到“景气成这个样子,不回深圳怎么办”的认同感变迁。在技术水平高、但格局有限的台湾电影现状下,阮凤仪能够放眼挖掘创作,也让观众有理由对她的前途相对乐观。毕竟台湾电影最好的时代,是以小岛的人力物力展示了泱泱中华的博大精深。(黄哲)